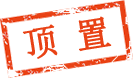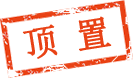“郭老是革命文化的班头”,这是周恩来谈及郭沫若的一句话。贬乎褒乎?言者应该是褒多于贬。不过,现在读来,“班头”二字却大有玩味之处,是文化的“领头羊”抑或戏班的头儿呢?
建国后,郭沫若几任中国文联主席,官居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之职。到今天,郭沫若与鲁迅、茅盾尚被称为文坛三大巨匠,加上其显赫的政治头衔,不可不谓为中国“第一文人”。而这样的一个“第一文人”一生中向这殊荣作出了何种表率呢?
1927年郭沫若邀请鲁迅一起向“旧社会进攻”,恢复创造社的《创造周报》,1928年却署名“杜荃”发文《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恶意地攻击鲁迅。当然,斯时毫不知情的鲁迅一一回应,却留给后世一场精彩且荒谬的论战;1948年3月,郭沫若发表了《斥反动文艺》一文,文中斥道:“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将沈从文定为“桃红色”的“反动”作家。
以上二事皆发生在建国前,郭沫若尚未获得“第一文人”的殊荣。但是从历史和后人给鲁迅及沈从文的评价及一些事件的真相,可窥大玩文字游戏的郭沫若其人格分裂的一面。
郭沫若一生当中,最为荒唐且可悲的时期是在“文革”期间,为傍江青这高枝,不惜穷其精力写出《武则天》以搏欢颜,而“四人帮“一倒台,郭氏又马上推出《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一词。前后相比,不禁让人为这“第一文人”的“变色”功夫拍案叫绝!尤为可笑的是,身为“第一文人”的郭氏竟写出“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样令人忍俊不禁复又顿感可耻的诗歌!“文革”期间,郭氏一边在王府大院里写着肉麻又可耻的“欢歌”取悦江青等人,另一边又“正义凛然”炮制一篇篇讨伐55万可怜的“右派”的檄文。
爱默生说过:“人文知识分子不应该把对知识的追求当作获取报酬的职业。追求知识和真理是不可能为他带来任何世俗世界中的物质利益的。他只能依赖另一些职业生存,例如充当灯塔守望者。”
爱默生这话,让我想起好多,远者如意大利的布鲁诺,为了学术的尊严被罗马教皇活活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近者有因《新人口论》而饱受折磨的马寅初及一生挺着腰杆走来的鲁迅等等。所有的这些人,虽然死了,但他们会永远活在后世人的心中。
回想前文的“班头”,呵,一介戏子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