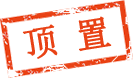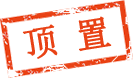“如果我们保护母亲是错的,那凭什么要我们保护拟喻意义上的“母亲”——祖国?如果保护了祖国后,我们自己的母亲都得不到保护,那祖国还是“母亲”吗?”
“如 果救母者被判无期,当初为何要抗日?”
在刀刺辱母者案上,熊培云老师用了这么句话作为评论的标题。
这句话糅入了最基本的世俗情理:如果我们保护母亲是错的,那凭什么要我们保护拟喻意义上的“母亲”——祖国?如果保护了祖国这个母亲后,我们自己的母亲都得不到保护,那祖国还是“母亲”吗?
“如果被侮辱者得不到法律保护,那法律还有何意义”的质疑,语义上也与此同构。
都是反抗入侵者,都是对抗恶。凭什么辱我祖国()母亲者,虽远必诛;辱我母亲者,“不存在防卫紧迫性”?假如人民在抗日时也被来一句:你们不存在反抗的紧迫性,那“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还能“起来,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吗?抵御外辱,不就是为了“保家卫国”吗,什么时候变得只能奉命“卫国”,不能有尊严地“保家”?

这些问题,当然不是刀刺辱母者案上的办案者应回答的核心议题。
他们要回答的,是刀刺辱母者的于欢,到底是不是正当防卫?对他是否该定罪量刑?办案民警渎职失职,可怕的高利贷和禁锢人身自由的讨债方式,是否构成抗辩事由?……案情细节和法理依据,是他们对“法治正义”做出交代时必须直面的。
但人们秉持的是“结果导向”:若法律不能保护人们,则人们只能违法。若司法不能给人民以正义,那被逼到死角的人们,只能奉行原始正义。
因为没得选择。
这也是人们一边倒地声援22岁的“杀人者”于欢的理由:他当时已没得选择。左边是地狱,右边是监狱,让他怎么选?不反抗,窝囊废;反抗,暴力罪,让他怎么选?
这要是在武侠剧或警匪片里,答案是明摆着的:反抗,不反抗毋宁死。所以乔峰要报仇,林平之要报仇,边城浪子要报仇。
“父之仇,弗与共戴天”,这是存诸人们内心的、关于大是大非的“自然法”。
而对父母几近当众淫亵的羞辱,显然在不能忍之列。
在佝偻活着、信奉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的国人心里,或许很多屈辱都可以忍,韩信“大丈夫甘受胯下之辱”大概没少被高中作文援引,“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鸡汤,就煨在犬儒人格的瓦罐里。
但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忍终有底线。“忍字诀”可以招待很多事,被殴打、辱骂,忍辱负重活着,没事。但当流氓要将生殖器塞到了自己母亲脸上和嘴里,如果再忍,无法想象,于欢会如何面对接下来的人生?
这是比刀架在脖子上胁迫还要命的事。
这也是近乎最高程度的恶。
这还是被捅死的讨债头头杜志浩的死,无法获得同情——哪怕是一点点同情的原因所在。
该事件中几个细节耐人寻味:杜志浩被捅了后,自己开车去了医院,还因琐事在医院门口跟人吵了架(所以失血过多,确定不是自己作的);杜志浩此前曾开车撞死女学生,导致后者身首异处,他肇事后逃逸,结果警方说找不到他人,其父母赔了28.5万元;这次,杜志浩家属向于欢家人索赔800多万……
这些让我相信:恶是有原因的,恶也是持续的。
这种人的恶,何曾逊于那些敌寇过?
这样的恶,又该由谁来治?
答案很明了,可现实很狰狞:本该治理这种恶的法,却最终治了以私人救济方式治了恶的人。
这让人难以接受:流氓不可怕,流氓有文化也不可怕,怕的是有文化的人拿着法典耍流氓。
判决于欢无期的当地一审法院,可能会拿出很多法律条文,佐证于欢有罪。
但“法者,平之如水也”,执法司法该一碗水端平:有律师就说了,于欢的母亲苏银霞借贷利息“月息10%”,根本不受法律保护;根据债务的相对性,吴学占以外的任何人根本无权向苏银霞讨债,纠集一伙人讨债,根据最高法《关于对为索取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拘禁他人行为如何定罪问题的解释》,应依照非法拘禁罪定罪处罚;当面猥亵、长时间无底线辱骂等行为,已达到了我国《刑法》中关于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立案追诉标准。这时候,法在哪里?
在公众印象中,有些法似乎总是治黎庶小民的,那些人想执法,你再小的问题,都会被依法处理;那些人不想较真,再大的问题,都可能找到法律漏洞去庇护违法者。你看看,有多少官员犯了罪,却迟迟逍遥法外;而有些微博骂官员的情况,警方一逮一个准,不含糊。
法,就是这么被某些人玩坏的。
所以比“假如你是于欢,面对母亲受辱该怎么办”更紧迫的问题是,“假如你是于欢,在危急时想求救于警方而不得该怎么办”。
后者才是刺痛人心之处:我们不一定会遇上讨高利贷的、耍流氓的,但一定会跟公权部门打交道,一定会找他们救济权利。
所以互撕成习、共识越来越难弥合的舆论场,才会罕见地一边倒为于欢鸣冤,因为它可能影射了我们普通人的遭际,它有着“我们都可能变成于欢”的代入空间。
我们无法言之凿凿地断言,当地法院在裁决于欢无期时,问题到底出在哪。可我们知道,如果一个判决连“良善”等指针都无法与民意对表,那一定是哪出了问题。
就像我们知道,一个失去了惩恶功能,却会惩罚惩恶者的执法司法体系,一定是病态的。
这种病态,才最可怕。
来源:仲鸣
|